清雍正某年正月,安老爺一行人出京南下,這日途經涿州城,見鼓樓西有座天齊廟香火鼎盛,便也跟著人潮來到廟內閑逛。只見正殿之前,大眾們燒完香、磕完頭,卻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得滿地,咱們踢來踹去,滿不在意。
老爺一見,頓時老邁的不安,嚷道:“阿阿!這班人這等作踐先圣遺文,卻又來燒什么香!”說著,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里焚化了。”華忠一聽,心里說道:“好!咱們爺們兒今兒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也不知是撿窮來了!”可是主人叮嚀,沒法兒,只得咱們胡擄起來,送到爐里去焚化。老爺還恐怕咱們揀得不凈,自己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麻花兒,也毛著腰一張張的揀得不了……
這個生動的片段出自晚清小說《兒女英雄傳》。故事中,被世人笑作“書白癡”的安學海老爺是一位通曉四書五經、深受儒家禮教浸染的品德榜樣。以現代讀者的視角來看,咱們好像很難讀懂蹲在香爐前撿拾字紙的安老爺的內心世界;但在明清時期的文學敘事形式之下,安老爺的行為卻非常“天經地義”。用作者文康的話來說,安老爺發的這些呆,“倒正是場‘勝念千聲佛,強燒萬炷香’的積德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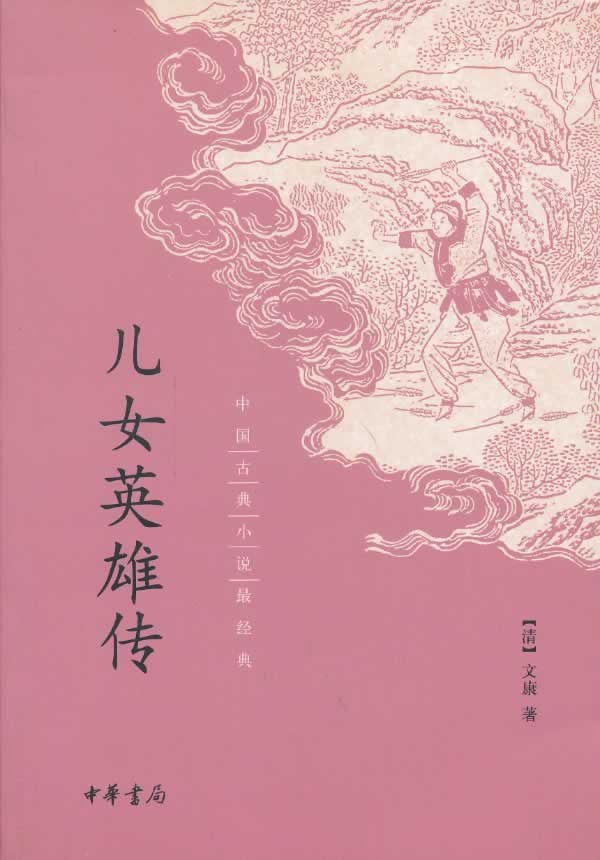
《兒女英雄傳》
不愿“作踐先圣遺文”的文明心思,早在南北朝時期(5—6世紀)就已呈現。聞名的《顏氏家訓》中清晰訓誡:“吾每讀圣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名字,不敢穢用也。”這種“不敢穢用”的心態,當然出于對圣賢辭旨的敬意,而另一個重要原因亦在于其時“故紙”寶貴,以至于不管官方、民間,都被逼催生出運用“反故”的習俗(即重復使用廢紙反面)。南齊的文人沈驎士,年過八十,家中藏書遭焚,不得不親手用廢紙謄寫書本多達兩三千卷;敦煌出土的很多文獻和宋代用于印書的公函廢紙也印證著這段綿長且無法的“反故”年月—敬惜字紙的情結,大約正是由此而生。
到宋代時,跟著常識獲取難度的下降,科舉考試向越來越多的中下層學子打開懷有。紙張和書本在日漸遍及的一起,“高中進士”的尋求也成了一種集體心思。一方面,科考內容的廣泛性讓人們認為不管何種書本簡直都是有用的,保護文字紙張成了金榜題名的根底和條件;另一方面,劇烈的競賽也促進很多考生把鋒芒畢露的機運押在各路神佛菩薩上,期望靠平常“與人為善”來交換果報。釋教和道教也紛繁經過各種勸誡故事宣傳敬惜字紙的必要性,尤其是聲稱“科舉之神”、兼掌司命和功名的文昌帝君,水到渠成地在線播放貴妃還鄉成了廣闊學子的請求目標。
明代時,跟著善書、寶卷(如《文昌帝君勸敬惜字紙文》《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的盛行,“科舉中第”與“珍惜字紙”被嚴密聯系起來,由此還催生出一系列筆記小說,為兩者的因果關系賦予傳奇顏色。最具傳奇性的莫若明末小說集《西湖二集》中的趙雄,據傳此人天分愚魯,像《千字文》這樣的啟蒙讀物,趙雄背了好幾天,就只記住開篇“六合玄黃”四字,連“世界洪荒”都接不下來。可趙雄人雖愚笨,卻忠誠發心,把字紙視同瑰寶一般,自忖“我終身愚笨,為人厭憎,多是前生不吝字紙之故。此生若再不吝字紙,連人身也沒得做了”。之后,這白癡竟因“陰功浩大”而感動了文昌帝君。在神仙的保佑下,趙雄一路連蒙帶撞,奇跡般地考中了進士,最終乃至官至宰相,成了蘇軾詩中“希望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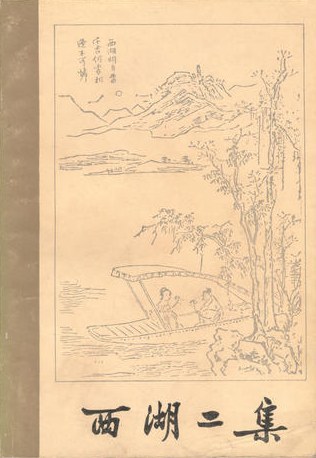
對字紙的尊敬不只能保佑愚笨之人高中,還能惠及后代后代。在老邁眾的認知中,北宋名相王曾便是因其父親敬惜字紙而得此善報的。傳說“但凡污穢之處、垃圾場中,或有遺棄在地下的字紙,王曾父親定然拾將起來,清水洗凈,晾干焚化,投在長流水中,如此多年”。某日,王曾之父夢到孔圣人下凡,稱“汝家珍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天主,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有非常”。之后王家公然喜得麟兒,而由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的曾子轉世投胎的王曾也水到渠成地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
趙雄與王曾在《宋史》中都實有其人,他們宛如“開掛”般的人生閱歷當然與傳奇故事臆造的“因果”毫不相干,但在明代大眾的心目中,敬惜字紙的行為已然褪去了開始珍惜物資的初衷,轉而成為一種獲取個人利益的手法,就像《文昌帝君勸敬惜字紙文》中教諭的那樣:“調查古今,當發跡之家,高官厚祿,無一不由祖上積功累行,敬惜字紙之果報。”
到了清代,敬惜字紙帶來的果報乃至超出求取功名這個單一維度,演變為全部塵俗希望,包含驅鬼、辟邪、免災、延壽、致富乃至求子。清代筆記小說中,有的人在線播放貴妃還鄉“向不讀書而偏知惜字”,除了撿拾字紙,還總能撿到銀錢、首飾等意外之財。有人因“平生惜字”,常常遇到飄搖欲墜的告示、廣告都要“檢藏回家”,因而就算深夜遇到“鬼打墻”,也能如有神助,平安無事。不單字紙有“法力”,字紙燒成的灰也有奇效。據傳濱海習俗,船員出海前都要特意去購買字紙燒成的灰燼,包裹好后作為護身符帶著出海,一旦遇到怪風、水怪或大可吞舟的怪魚,把紙灰投入水中即能平安無事。乃至還有“連生五女,八年不孕”的婦女因終年出錢收買字紙而“胎得一子”的奇聞。在釋道兩教的大力烘托下,清代大眾不只信任敬惜字紙能保佑“后代連捷,名登仙籍”,就連“身列仙品,永脫輪回”也不在話下。
這些看似和紙張自身八棍子撂不著的“訴求”,都可以經過敬字惜紙得以完成,這恐怕是顏之推締結家訓時萬萬沒有想到的。南北朝時被視為寶貴物資的紙張,現在被大眾們當作符咒般的“法器”,清洗潔凈、燒成灰燼,再埋入土中或投入清水,過程中充滿了功利主義和典禮顏色。而撿拾字紙也儼然與謄寫經文相同,被老邁眾簡化成了一種堆集積德行善、完成希望的手法—只需彎折腰就可做到的工作,何樂而不為呢?
晚清光緒年間,出使歐洲列國的郭嵩燾、薛福成等大臣見到西方人“身坐車中,閱新聞紙,隨閱隨棄,任其投擲于水溝污穢之中”的大不敬之舉,感到非常震動。惜紙思維根深柢固的郭嵩燾在出使期間參議禁煙和公約事宜之暇,還不忘苦口婆心地勸誡西方官員要珍惜字紙,卻發現對方底子不妥回事,直言除了“耶穌教學”,“諸字書皆可遵從蹂躪”。回到寓所后,這位我國首位駐外青鳥使深感洋人社會現已根深蒂固,還在日記中怒火中燒地寫道:“人心已成積習,則非善言所能入也!”

郭嵩燾
當然,咱們沒有理由苛責19世紀的歐洲人穢用紙張,究竟,就算是才高八斗、終身惜紙的安老爺,也未必可以觀察幾個世紀以來我國紙價沉浮背面的經濟邏輯與崇奉變遷。在安老爺、郭嵩燾和廣闊我國大眾眼中,不管紙上寫的是漢字、拉丁文仍是阿拉伯數字,珍惜字紙不都是水到渠成的工作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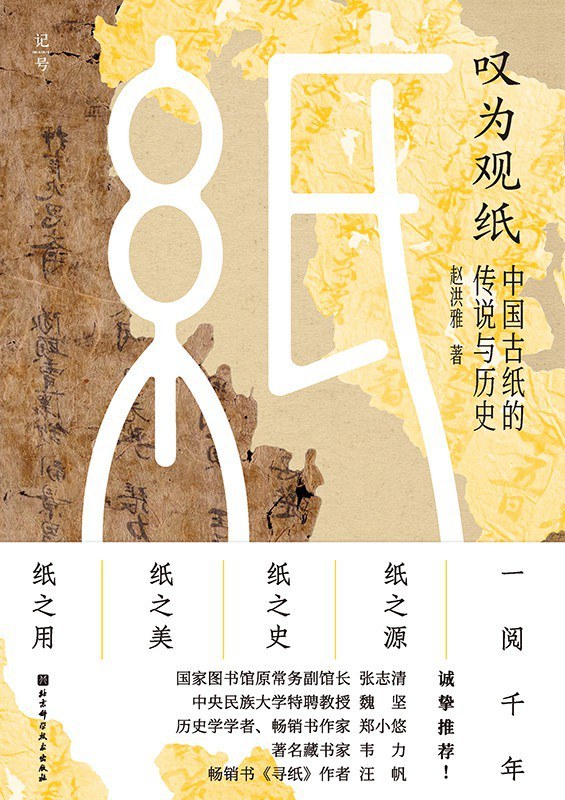
本文節選自《嘆為觀紙:我國古紙的傳說與前史》 (趙洪雅 著,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 記號Mark,20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