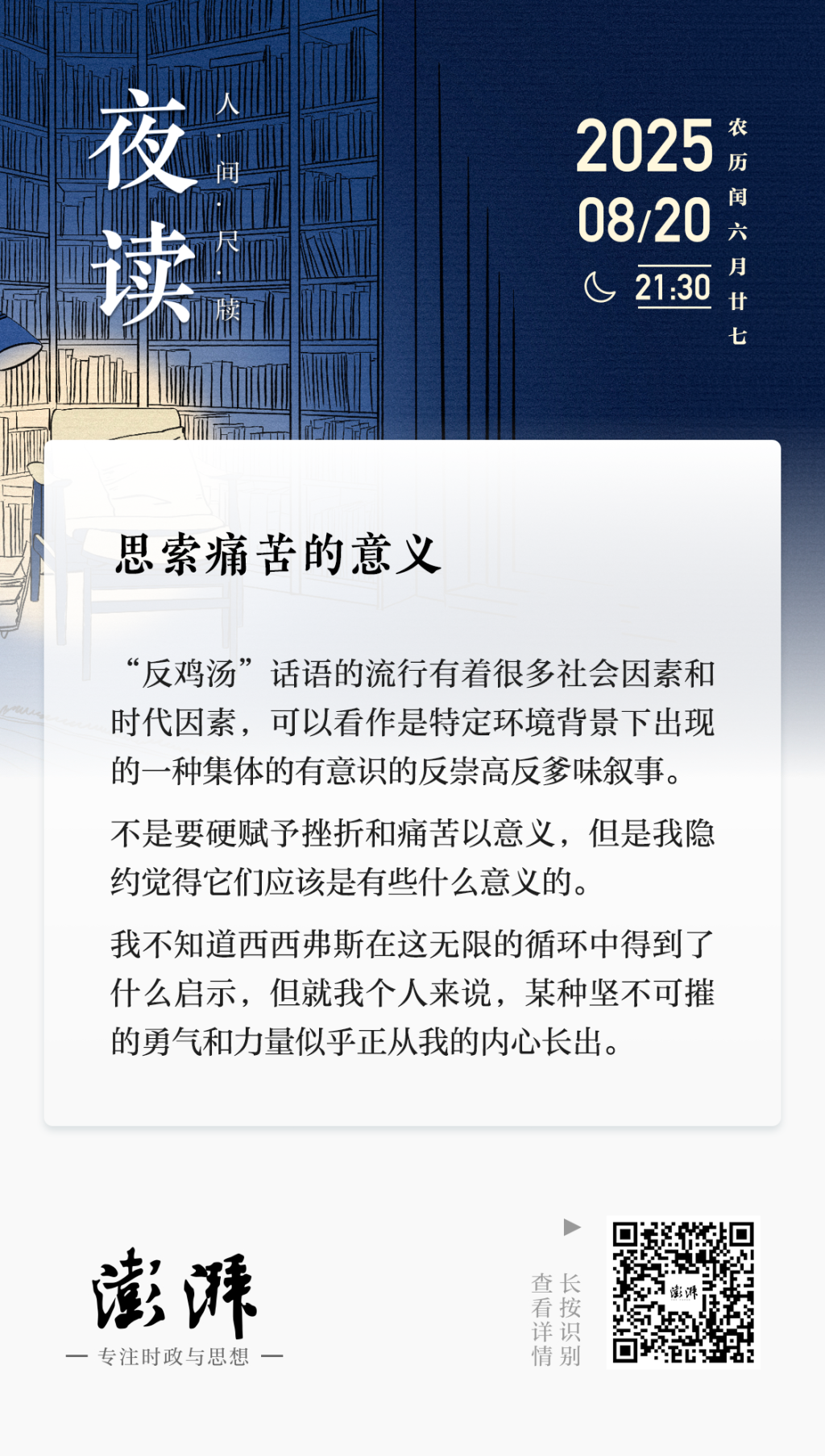不知從什么時分起,“磨難和波折毫無含義”“成功才是成功之母”這類反傳統雞湯言語忽然盛行起來。
這種所謂“反雞湯”言語的盛行有著許多社會要素和年代要素,能夠看作是在特定環境布景下呈現的一種團體的有意識的反崇高反爹味敘事。大約是那個時刻把握了網絡言語權的人,對自小所受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類磨難教育的抵擋和嘲諷,舉例來說,“能喫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便是最具殺傷力的反擊。
我很長時刻以來也持相同的觀念,磨難毫無含義,企圖從中總結經驗取得含義的全部做法都是人對自己所遭受的不幸的美化,一種心思自我維護機制,一種精神勝利法。假如能夠一往無前,誰還愿意喫苦?
尤其是近些年,不知道是網絡過于興旺仍是其他什么原因,實際中有那么多人在閱歷本不應閱歷的磨難,讓我越來越堅定地不斷勸自己及身邊的人,千萬要摒棄從磨難中尋覓含義的陋俗。
但一起,我心里又有一種模糊的置疑,真的是這樣嗎?沒有波折沒有苦楚的人生真的愈加有含義、愈加美好嗎?回頭又看到那些正在閱歷戰役、虐待、意外的人,我對我有這樣的置疑感到慚愧。在這些人面前,以上疑問不只毫無含義,乃至充滿了無知和高傲。
如此想來,咱們大部分人在人生里遇到的大部分不如意和苦楚應該都用不上“磨難”這么嚴峻的描述,應該只能當作是“波折”。
不是要硬賦予波折和苦楚以含義,可是我模糊覺得它們應該是有些什么含義的。gay文h甲方的刁難、乙方的不合作,被降薪被裁人,分手、離婚,老友反目、同室操戈,破產、患病,乃至包含現在被許多人掛在嘴邊的“原生家庭問題”等等,以上這些終將會在咱們的人生旅途中呈現的問題——有些現已呈現并將重復呈現,必定有它存在的含義和價值,不然,咱們的人生有什么含義?
拋開幸福高興究竟是不是暫時的、究竟是不是人生悲慘底色的副產物,以及人生底色究竟是什么色等問題不談,與成功之母究竟是成功仍是失利這種觀念之爭不相同的是,咱們當然能在幸福高興中得到許多,但不可否認,某些自我體恤和深觸魂靈的反思,或許只要在苦楚中才干進行。
我想咱們大約總會在某一次求高興而不得或許屢次受挫之后,開端考慮為什么會是這樣,為什么總不能得償所愿,老話說的公然沒錯,“日子不如意十之八九”。
高興與苦楚輪流呈現,咱們突然發現相同的“我”,在不同的境遇下竟然是如此不相同。不高興的時分開門見陽光都覺得扎眼,高興的時分途中遇暴雨也是浪漫。然后才漸漸了解,外界其實是心里的投射。gay文h
在這之后,大約還要閱歷許屢次潰散和苦楚,才干較為鎮定客觀且殘暴地、抽絲剝繭一般,看到自己、反思自己,我是怎么對待自己和別人、怎么被別人對待的,怎么得意洋洋,怎么怯弱。
這時才意識到,人之復雜性、與人共處之復雜性好像是一種謬論——與人共處好像很簡單,無非便是用心看見并領會別人的喜與悲,坦白面臨自己的喜與悲,識別到所有人的真摯,并為此感動,也更了解與之相伴的虛偽,并為此感到深深的哀傷。然后知道怎么維護自己,怎么不損傷別人。
如此這般“遇到波折-感觸苦楚-在苦楚中打破又重構自己”的循環大約只會在生命的結尾才會完畢——公然,咱們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我不知道西西弗斯在這無限的循環中得到了什么啟示,但就我個人來說,某種堅不可摧的勇氣和力氣好像正從我的心里長出。
在我醍醐灌頂般想理解了這全部之后,我才了解了,博爾赫斯“你有職責跟我們相同/坦蕩而高興/你有必要自己解救自己。假如你還有什么差錯的話/那就讓我來承當吧”這句詩里巨大的悲憫。